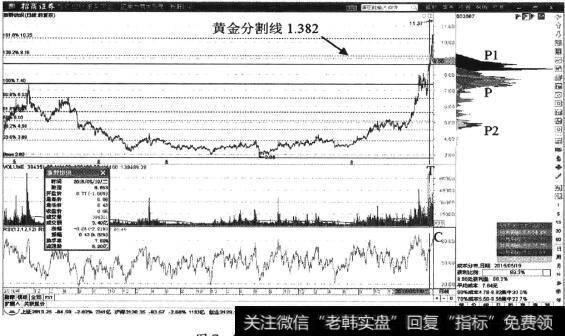|
第一百零一节
日耳曼蛮族在西罗马境内的存在
附:日耳曼蛮族统治下的西罗马(公元507年)
多西哥特人攻入罗马(公元410年),到罗马帝国正式消亡(公元476年)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日耳曼罗马”时代。对于生活在西地中海的罗马人来说,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这个国家已经被他们眼中的蛮族——日耳曼人所控制了。首先日耳曼人的举族入侵,已经造成了西罗马的事实分裂。那些被日耳曼人割据的土地,虽然表面还会奉罗马这宗主,但从内政、军事、法律等各个层面看,都已是完全独立的了。比如在“日耳曼罗马”时代,帝国内部出现了罗马、日耳曼两套体制。罗马人适用罗马的法律,而日耳曼人则适用日耳曼人的法律(如果可以称之为法律的话)。套用一个出现在20世纪的名词,就是“一国两制”了。
其次由于罗马军队本身,也已经严重依赖那些蛮族出身的将领了,所以那些进入罗马政治体系的日耳曼人,对西罗马中央政府的掌控力度也越来越强。以至于到后来,罗马皇帝完全成为了日耳曼军人的傀儡。之所以暂时还奉着这个神祖牌位,一是因为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要让罗马臣民适应新的国家,也需要一个过程(虽然肯定比建成的时间短的多)。“三代”和“一甲子”,是我常用给大家参考的时段。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对比一些历史上的过渡时期,看看是不是符合这个规律(比如公元220年——280间的三国时代);二是日耳曼人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分散的部落体。如果想取得对其他日耳曼人的比较优势,暂时保留一个受自己控制的旧体系,能够事半功倍(参考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既然端坐在罗马城中的皇帝,到底是谁已经不重要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应该把重心,放在日耳曼人是怎么在西罗马境内“裂土封王”的问题上了。可以预料到的是,这个过程并不会太和平。其实这也正常了,既然整体感要强的多的罗马,都免不了内战,又怎能期待那些日耳曼部落首领们,能够和平的坐在一起谈未来的领土划分呢?我们当然不用去追溯每一个日耳曼部落的源流和渗透路线了。因为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真正能够被青史留名的,并留下地缘遗产的只是少数。
首先出场的是一支特别的混合势力:汪达尔——阿兰人。这一组合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是由罗马原本安排在潘诺尼亚的日耳曼蛮族“汪达尔人”,与被匈人击败西迁的游牧民族“阿兰人”联合而成的。从技术上看,这样的组合确实能够取长补短。汪达尔人可以从阿兰人那里得到机动力,而阿兰人向西徙入日耳曼人的势力范围时,也不至于有孤立感。
在短暂入侵意大利之后,汪达尔——阿兰联盟和其他的日耳曼蛮族一样,将下一步的方向定位在了高卢。不过高卢也是其他日耳曼尼亚部落入侵的首选之地,尤其接下来攻入罗马的西哥特人(并获得部分罗马军队的支持),同样把自己的建国之地,选在了高卢南部。有鉴于此,汪达尔——阿兰联盟很快便识时务的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入驻西班牙。然而这个计划很快便被打乱了,因为在众多日耳曼部落从北方涌入高卢的大背景下,即使西哥特人当下的实力最强,也不可能占据整个高卢。在向高卢北部扩张无望的情况下,西哥特人也把西班牙作为了自己下一步的扩张方向。
最终让双方达成平衡的,是那条分割欧、非两洲的“直布罗陀海峡”。公元429年,汪达尔——阿兰联盟跨过海峡,出现在了北非的土地上。十年之后,罗马彻底退出北非,将那些受阿特拉斯山脉滋养的绿洲“让”给了汪达尔——阿兰人建国。汪达尔——阿兰王国(由于王室是汪达尔人,也被称为“汪达尔王国”)的版图,基本就是迦太基早期的翻版,其控制区大致相当于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中东部的沿海地区。至于阿特拉斯山脉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南岸,则为北非土著所控制。这些土著,现在被称之为“柏柏尔人”。其种族属性与阿拉伯人一样,随着阿拉伯人对北非的控制,大部也为之所融合。当年曾经在布匿战争中大出风头的努米底亚王国,也是由他们所建立的。
虽然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之前都是大陆民族,但人是会适应环境的。就像后来建立庞大帝国的蒙古人,也建立过海军入侵日本一样,在迦太基故地上立国的汪达尔王国,很快也建立了自己的舰队。并且乘欧洲大陆一处混乱之机,控制了西地中海当中的众多岛屿(西西里岛、科西嘉岛、撒丁岛,以及巴利阿里群岛),甚至在公元455年,一度攻陷了罗马城。当然,这一切很显然都是利用了本地资源。就像蒙古人也不是自己从马上下来造船一样。不过偏安一隅的汪达尔王国,命运也注定和迦太基人一样,不可能成为欧洲之主了。
将汪达尔——阿兰人赶到非洲之后,西哥特人获得的西班牙的统治权。加上在高卢南部的领土(包括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之间的沿海通道,以及比利牛斯山脉北部的加龙河流域)。西哥特王国为自己谋得了一个颇为有利的地缘位置。一方面能够直接威慑意大利的西罗马中央政府;另一方面还有机会向高卢腹地扩张。对比之前在多瑙河下游所的两面受敌境地,可谓是天壤之别。假如西哥特人能够再控制整个高卢,他们接下来很可能就会直接入主意大利,替换掉傀儡一般的西罗马皇帝了。
自凯撒从高卢而兴,建成罗马帝国以来,每个试图夺取帝国控制权的人,都很清楚高卢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西罗马帝国宁愿将西班牙交给西哥特人,也不愿意失去高卢的主控权。在西罗马帝国存续期间,整个高卢地区最有种植潜力的“巴黎盆地”(塞纳河流域)都还在罗马的直接控制下。西哥特人在高卢的领土范围,则被控制在了卢瓦尔河以南地区。问题在于,高卢的不稳定因素并不仅仅来自于南方,觊觎高卢的也不仅仅是西哥特人。要知道,一直以来,日耳曼人都在尝试渗透至莱茵河西岸。如今碰到这样一个大好时机。指望来自日耳曼尼亚方向的部落,指望莱茵河防线不被突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在经历最初的混乱之后,及至公元5世纪中叶,高卢东、北边境被三股日耳曼势力所控制(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我们下节会分析)。由南至北分别是勃艮第人、阿拉曼尼人,以及法兰克人。三股势力的分布,也颇符合地缘规律。其中勃艮第人得到了包括索恩河、瑞士高原在内的罗纳河流域(除了西哥特王国控制下的下游的沿海平原);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在内的,莱茵河中游地区则成为了阿拉曼尼人的领地。至于法兰克人,则成为了莱茵河下游,比利时高卢的主人。由于这些日耳曼人,本身就是来自与罗马相邻的日耳曼尼亚地区,所以他们所建立的日耳曼王国,同时也对应包含了大片莱茵河东岸的领土。
在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之前,上述日耳曼人和西哥特人一样,都得到了罗马方面的承认,并以盟友的形式生活在帝国的名义版图内。只是大家都明白,罗马的这种承认是在无奈接受现实。当然,这种格局也并非一点好处都没有,最起码这些被允许定居的帝国边境地区的日耳曼人,出于保护“既得利益”的原因,会阻止其他日耳曼人继续给高卢地区造成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存在于今天法国北部的那块“飞地”,所承担的战略任务,更多是在维持高卢境内四大日耳曼势力之间的平衡了。
其实以西罗马在高卢的直属地为中心环顾四周,我们会发现这些身处高卢的罗马人,所需要平衡的力量并非四股,而是六股。这使得这片罗马飞地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中原之地”,日后谁要想成为高卢之主,就看谁能够有力量先入主中原了。至于还有两股力量是谁,我们下节再接着解读。
第一百零二节
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凯尔特人
附: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地缘政治格局(公元480年)
中国历史也曾经出现过类似于“蛮族罗马”时代的情况——“春秋”时代。二个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这有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另外就各路蛮族大规模入侵,导致割据局面这一点来看,又与稍早发生在东亚的“五华乱华”时代如出一撤。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还有哪支蛮族,借势出现在了欧洲地缘政治舞台上。
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不列颠,曾经是罗马帝国的最西境。为了应对西哥特入侵所带来的混乱局面,罗马最终放弃了这块海外之地。理论上,一直被罗马压制在西、北部高地的凯尔特人,应该有机会出头了。然而事实却是,日耳曼人也同样没有放过这些岛屿,他们当中的一些成员,很快便在不列颠群岛,拉开了一场长达千年的民族恩仇录。这些入侵不列颠的日耳曼人,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英格兰人”的祖先。单从名称也能猜到,英格兰人的祖先,应该是由两支日耳曼部落混合而成的。其实参与开拓不列颠的日耳曼部落,并不止于盎格鲁、撒克逊两族,最起码还有一个朱特族发挥了同等的作用。这支不为大家所熟知的日耳曼人,原居于日德兰半岛的北部,也就是今天的丹麦境内;半岛南部是盎格鲁人的领地;撒克逊族则是从中欧平原西部,易北河、威悉河下游起程的。以上述三族在不列颠的后裔为主,融合而成了
“盎格鲁——撒克逊人”。
对辛布里战争还有印象的朋友,应该已经意识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的故地,与辛布里人、条顿人、阿姆布昂人几乎完全重合。与那次日耳曼人的不请自来不同的是,最早生活在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等日耳曼人,是在公元5世纪初,以雇佣军的形式被罗马人主动迎入的(大多入侵罗马的日耳曼蛮族,都有过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状况的大背景是,在帝国决定放弃不列颠之后,很多身处不列颠的罗马人,并不愿意回到大陆。毕竟罗马经营不列颠已经有300多年了,对于绝大多数不列颠罗马人来说,这里才是自己的家(尤其不列颠最好的的土地大多在他们手中)。为了不被仇恨罗马的凯尔特人所吞没,盎格鲁、撒克逊等族的雇佣兵被从对岸招募了进来。
日耳曼蛮族大规模向不列颠迁徙,是在公元5世纪中叶。大量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沿海岸线西行,在征服比利时、荷兰境内的低地(比荷低地)后,再渡过英吉利海峡进入不列颠。虽然先期在不列颠立足的雇佣兵们,肯定算是指路人了,但从大的地缘背景上看,这其实也是个必然选择了。同500多年前启程的日耳曼三族相比,盎格鲁、撒克逊、朱特三族并没有先发优势。那些紧邻罗马的日耳曼部落,会更有机会进入罗马,并成为后来者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渡海进入不列颠成为了这些北方部落的最好选择。
上述三族也并非全部迁入了不列颠。今天我们在德国西部仍然能够找到三个以“萨克森”为名的州(萨克森州、下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特州)。所谓“撒克逊”、“萨克森”的不同,只是中国人为了方便区分他们的地缘属性,刻意根据英语、德语发音作出的不同的翻译罢了。另外“比荷低地”
也有这次跨海迁徙留下的遗民。那些留驻于此,未能渡海的迁徙者,被称之为“弗里斯兰人”。
以盎格鲁、撒克逊等族的迁徙路线来看,我们应该很有机会在后来的历史中,看到一个以“北海”为核心,包括不列颠、比荷低地、日德兰半岛等大西洋海岸地区在内的“北海王国”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不管盎格鲁人、撒克逊人,还是朱特人,都只是基于语言、文化、血缘等特征定义出的民族集团。被打上同族的标签,并不代表拥有统一的政权结构。由于与地中海文明的地缘距离较远,这些英格兰人的祖先,在当时仍然是分散的部落结构。其迁入不列颠的行为,也没有统一计划,而是在数十年时间内,不断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的。这也意味着,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仅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北海王国”,甚至在不列颠的融合,所需要的时间也远较欧洲的日耳曼人来的慢。
第一阶段的融合,大约花两百年时间。至公元7世纪时,这些生活在不列颠的日耳曼人,逐步整合成了七大王国,史称“七国时代”(追美剧《权力的游戏》的朋友是不是觉得眼熟)。在这个过程及以后的历史中,那些身为不列颠土著的凯尔特人,始终是这些日耳曼人的最大对手。发展到后来,就是英格兰和以苏格兰为代表,包括威尔士、爱尔兰在内的,凯尔特系民族地区之间的恩怨了。
一般现在提到凯尔特人,大多数人马就就会想到上述三个地区。不过事实上,当下仍然有资格被认定为是凯尔特文化区的版块,一共有六个。包括: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马恩岛、康沃尔,以及布列塔尼。能够在如果漫长的岁月里,为曾经占据大半外欧洲的凯尔特人留下一些火种,与上述地区的地理结构、地缘位置有直接关系。以大家熟悉的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为例,前两者能够不被罗马人、日耳曼人所融合,得益于它们的高地地形、沿海位置。高地为这些凯尔特人及其后裔提供了保护,海洋则为彼此的互联互通提供了渠道。
马恩岛是位于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英格兰之间的,不列颠群岛第三大岛。所谓“英伦三岛”之说,就是源自大不列颠岛、爱尔兰岛、马恩岛。在能够与周边三大凯尔特板块互动的情况下,日耳曼人想融合这块跳板是很困难的。至于康沃尔和布列塔尼,则是分列于英吉利海峡西北、西南位置的两个半岛。前者当下属于英国,与威尔士、爱尔兰地区隔海想望(那片海就叫“凯尔特海”);后者则是五角形的法国,西侧的那个角。
康沃尔半岛能够成为凯尔特人的保留地,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毕竟它本身就处在欧洲最后的凯尔特人集中地。比较特别的是布列塔尼半岛,居然能够在西欧的拉丁化、日耳曼化浪潮下,保留凯尔特文化。事实上,布列塔尼人并不是在罗马时期就生存于此的。他们是在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不列颠时,反向迁入布列塔尼亚半岛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回家,因为不列颠的凯尔特人,本身也是在罗马征服高卢前迁徙不列颠的。同样由于半岛状的地理结构,以及与其他凯尔特地区的地缘距离,使得布列塔尼亚人在“日耳曼罗马”时期,有机会在欧洲大陆的西部,为凯尔特人获得一片保留地。
现在大家应该清楚了,西罗马帝国在巴黎盆地的存在,是要维持哪六股势力的平衡了。他们分别是北方的法兰克人、东面的阿兰曼尼人、东南面的勃艮第人、南面的哥特人、西面的凯尔特人,以及西北面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应该说,在整个“蛮族罗马”时代,罗马人在高卢的平衡还是维持的不错的。具中的位置,极大影响了西欧几大蛮族势力之间的整合工作。然而地缘平衡终究还是在四、五世纪相交阶段最打破了。不过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却不是在高卢,而是在意大利倒下的。至于是谁促成了这一切,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一百零三节
阿提拉帝国的崛起
一下子涌现出那么多日耳曼蛮族,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的朋友是不是有点一下子消化不了?其实即使是回首中国历史中的“五胡乱华”时代,又有多少人能准确点出是哪些胡人为乱中原呢?所以不清楚这些蛮族的历史,也没有什么打紧的。明白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并最后看看是哪支蛮族脱颖而出就行了。说到这,我们好像还漏了一支非常重要的蛮族势力,那就是与西哥特人一起退入罗马境内的东哥特人。前面我们已经交待过了,东哥特人被罗马安置到了潘诺尼亚,以帮助帝国防御来自匈牙利草原的威胁。因此,东哥特人能有多大作为,关键要看匈人的动向。
最初侵入南俄、匈牙利草原的匈人,内部权力其实还没有完全统一,或者说只是基于共同目的而形成的部落联盟。匈人内部完成权力统一的时间,大约与西哥特人攻入罗马的时间相当(公元410年)。虽然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喜欢将这个匈人帝国称之为“阿提拉帝国”,但最初完成整合工作的,其实是阿提拉的叔叔。被欧洲人称之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是在公元434年与他的兄弟共同继承帝国,并在445年达到事业顶峰的(刺杀共主,成为唯一君主)。
鉴于南俄、匈牙利两大草原都处在巴尔干半岛的北部,所以一直到阿提拉成为帝
国唯一君主之时,匈人的主攻方向都是南面的东罗马。对于匈人的这种选择,西罗马自然也是感到十分庆幸的。双方为此甚至还缔结了和约。年少时期的阿提拉,就曾经作为和约的保证,在西罗马宫庭生活过多年(罗马方面也在贵族在匈人境内为质)。
由于有多瑙河这条经营已久的天然防线,东罗马/匈人帝国博弈的局面,很像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隔长城对峙的情况。匈人总体上属于战略主动方,并经常寻找合适的时机入侵东罗马,而处于防御方东罗马帝国,更多是在疲于应付。不过与当年生根于蒙古高原的匈奴帝国一样,进入欧洲的匈人也对转为定居生活不感兴趣,目的只是在劫掠。这些游牧者深知自己的根在草原。一旦远离草原定居、建国,就会最终丧失自身的优势。这一点在阿提拉本人身上也体现的很明显,虽然罗马希望用“文明”来同化这位未来的君主,但后来回到草原的阿拉提,这是坚持过着简朴的游牧生活。
尽管有多瑙河防线存在,匈人强大的机动性,还是对东罗马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换取匈人的和平承诺,东罗马最终选择了一个商业性的方案——“岁币”。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方式实在太过屈辱,不过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中也比比皆是,最为典型的就是宋、辽之间的“澶渊之盟”了。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说,这倒也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毕竟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会造成巨大的损耗。当然,同样做一件事,战略上想法却不尽相同。宋朝的做法,更多是在花钱买平安,而汉、唐在立国之初,对匈奴、突厥的隐忍,则是在韬光养晦。
从东罗马的想法来看,其实更像是前者,或者说并没有日后主动出击,解决草原威胁的决心。这倒也不能说东罗马过于短视,毕竟在它的东、西两面,还有两个与之同级别的对手:萨珊波斯和西罗马,地缘政治层面上的顾虑要更多。如果自己去死磕匈人的话,谁又能保证不被“两肋插刀”呢。在这种情况下,东罗马花出去的钱,就不只是买在平安,同时也是希望能够祸水东流(或者西流)。在阿提拉和他的兄弟上位之后,新生的草原帝国也的确曾经尝试过从高加索方向进攻波斯(为此东罗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把支付给匈人的岁币增加两倍),不过这次尝试并不成功。
纵观历史,匈人一直没有将波斯锁定为主攻对象过。究其原因,还是与匈人的地缘位置有关,毕竟他们已经西迁至欧洲草原了。此时在中亚草原代表游牧民族执行南下任务的,是另一支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嚈哒”(yàndā)人。他们进入跨越阿尔泰山进入中亚草原的时间,与匈人出现在欧洲草原的时间一样,都是在公元4世纪70年代。基于时间以及地缘关系,嚈哒人与匈人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至于二者分占中亚、欧洲草原的格局,是和平协商还是战争的结果(更可能是二者皆有)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欧洲人倒是会将嚈哒人称之为“白匈奴”。
匈人在欧洲发力,并成为东罗马的最大威胁时,白匈奴也进入中亚“河中地区”,成为萨珊波斯的北方压力源。在其鼎盛时期,甚至复制当年大月氏人(贵霜帝国)的路径,攻入印度河流域。说起来,这真是一个欧亚草原的黄金年代,每个重要文明区,都必须思考怎样应对来自亚洲游牧者的威胁。尤其是匈人在欧洲的开拓,让欧洲人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游牧压力。这一压力不仅体现在东罗马身上,也体现在日耳曼尼亚。
相比罗马人坚固、系统的防御体系,部落体结构的日耳曼尼亚,显然缺乏防御匈人进攻的手段。尤其他们当中的很多部族,在匈人到来之前就已经闻风西逃了。唯一应该感到庆幸的是,鉴于匈人的游牧属性,他们对日耳曼尼亚的统治,也如当年匈奴控制西域时的情况一样,属于间接控制。那些表示臣服,并主要以农业立身的日耳曼人部落,本身的政治、社会结构并不会受到影响,他们所需履行的义务,主要向宗主定时交纳贡税,以及战时提供军事支持。
最起码在阿提拉时代,匈人已经能够在莱茵河畔饮马了。如果将东罗马帝国比作当年的汉帝国,那么日耳曼尼亚就是“西域”。只是对于匈人来说,这片欧洲“西域”与亚洲西域的地缘价值却不尽相同。西域之于匈奴,更多只是一块可以提供额外补给之地,而日耳曼尼亚则是通往另一片文明之地的桥梁。当整个日耳曼尼亚都在阿提拉帝国的控制之下时,大家会发现,西罗马与匈人的接触面已经远超东罗马了。
第一百零四节
阿提拉帝国的扩张和崩溃
从地缘结构上看,征服日耳曼尼亚之后的阿提拉帝国,已经取代日耳曼人,在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对地中海文明造成了全面的压力。当攻打波斯力有不逮,东罗马又愿意成倍增加岁币保平安时,西罗马遭受入侵的可能性无疑被大大增加了。就攻击方向而言,阿提拉帝国可以在高卢和意大利半岛中作出选择。综合考虑下,阿提拉选择了高卢。公元450年,阿提拉和他的日耳曼盟友们跨过了莱茵河。
促使阿提拉选择高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他之前曾经在罗马的请求下,派军在高卢与西哥特人作战过。另外,高卢一直是日耳曼尼亚的天然扩张方向。那些日耳曼尼亚部落之所以愿意臣服于匈人,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双方可以优势互补,共同从高卢获益。需要说明的是,罗马阵营也有大量日耳曼部族,甚至成为了军事力量的主力。甚至同一部族中,即有站在匈人一边的,也有与罗马结盟的。总的来说,先期获罗马允许进入高卢的部族,会更愿意将自己的利益与罗马捆绑在一起;而暂时未在西罗马衰退中获取利益的部族,则会希望借匈人的势分一杯羹。
看起来这种局面似乎让日耳曼人很尴尬,有点手足相残的意识。然而从地缘角度看,整个日耳曼民族却会是最终的受益者。如果罗马胜了的话,那么无论是在融入西罗马帝国体系日耳曼人,还是那些获准在西罗马境内居住的日耳曼部落,都会因此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反之,如果是阿提拉帝国全取高卢,直接受益者其实也是日耳曼人。基于匈人的游牧本性,他们认为定居生活会削弱自己的军事优势(事实也是如此)。同时匈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口来做到这点。换句话说,战后填补高卢人口真空的只能是日耳曼人。至于匈人,则会有意识的保持自己的游牧属性,以一个“军事民族”的形式,保有最高政治权力。
显而易见的是,就像在中国的情况一样,这种上、下分离的社会结构并不会长久保持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政权的游牧属性逐渐退化后。高卢最后还是成为日耳曼人的高卢。不过历史并没有机会让我们在高卢看到这一幕,因为匈人之前的恐怖攻击行为,虽然经常让他们的对手不战而降,但也可能使得他们对面的敌人变得空前团结。在西罗马的游说之下,高卢的日耳曼人都意识到了,必须放下彼此的矛盾,联合起来阻止阿提拉的入侵。甚至连小不列颠(布列塔尼半岛)的凯尔特人,也加入了联合阵营。
为西罗马方面提供最大支持的日耳曼势力,是先期已经获得高卢南部的西哥特王国。西罗马的外交家让西哥特人明白,如果罗马人被迫放弃巴黎盆地、退出高卢,那么接下来直面匈人的,就是一直在逃避这种局面的他们了。事实上,西哥特人已经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威胁了。除了派军进入塞纳河流域外,阿提拉亲自率领军队,出现在了卢瓦尔上游(奥尔良城)。说起来也是应了那句话:“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在此之前,匈人还曾经作为西罗马的盟友,攻击越来越尾大不掉的西哥特王国。
当高卢地区的军事力量都向巴黎盆地集结时,阿提拉也开始暂时放弃在卢瓦尔河的军事行动,转而准备在巴黎盆地与对手展开一场决战。对于希求速战的客军来说,这也正是匈人需要的。决战塞纳河上游的马恩河畔(今法国沙隆),史称“沙隆之战”。据称双方所投入的总兵力,都达到了50万之巨。总的来说,双方都损失惨重(战死率高达20%左右)。虽然西罗马方面声称自己是最后的胜利者,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联军方面的损失要小于匈人(西哥特国王甚至战死了),而是因为阿提拉决定结束高卢战事。
如果没有日耳曼人(高卢境内)的支持,西罗马很显然是没有办法对抗匈人的(兵力只有其一半)。然而现在的高卢,已经不是罗马一家的高卢了,阿提拉一定要进攻高卢的话,就势必会让高卢人同仇敌忾的。更为致命的是,匈人之所以能够征服日耳曼尼亚,很大程度并不是通过战争,而是威慑手段。一旦战争陷入拉锯状态,相比那些保家卫国的高卢日耳曼人,阿提拉军内的那些日耳曼人,会更容易出现动摇。
正因为意味到这一点,阿提拉决定放弃高卢,转而把兵锋直指意大利。很多“作家”在描述这段历史时,会把匈人入侵意大利描述为越过“阿尔卑斯山”,其实当我们脑海中有了地缘概念后,就会明白匈人并不会从日耳曼尼亚境南下,而是会退回匈牙利草原,然后向西穿越与之隔多瑙河相望的“潘诺尼亚平原”,从阿尔卑斯山脉与迪纳拉山脉交接处(斯洛文尼亚境内)攻入意大利半岛了。在这个过程中,唯一需要考虑的,是被罗马安置于潘诺尼亚的东哥特人。
其实东哥特人并不会给阿提拉带来麻烦,作为西罗马与匈人之间的缓冲地带,东哥特人一直是在左右逢源。部分东哥特人,甚至被允许居住在蒂萨河下游、匈牙利草原南部(算是人质了)。当然,东哥特人能做到这一点了,主要与匈人在战略上把攻击对象定为东罗马,并维持与西罗马的和平有关。当西罗马成为阿提拉帝国的攻击目标后,哥特人就必须选边了。
选边的结果毫无悬念,在阿提拉进攻高卢时,东哥特人就作为盟友,出现在了阿提拉的军队。当阿提拉把攻击方向调整为意大利时,东哥特人则因地缘位置,受益成为了阿提拉最为倚重的日耳曼盟友。不得不说,将入侵方向调整为意大利,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战略决定。因为在高卢之战中,罗马所依靠的那些高卢日耳曼人,之所以愿意与匈人为敌,完全是出于自保。要说服他们为意大利流血,就需要花钱了。更为致命的是,由于要维持高卢的地缘政治平衡,以防阿提拉退兵后,某支日耳部落借机做大(特别是西哥特人),罗马在高卢的驻军,甚至也不能大规模回援意大利。
公元452年,阿提拉和东哥特人的大军出现在了意大利的土地上。有如当年西哥特人的西征一样,入侵者如入无人之境般的横扫了波河平原。需要说明的是,罗马城此时已经不是西罗马的首都了。早在50年前,西地中海的政治中心就从意大利半岛西侧的罗马,转移到波河平原东南角的沿海城市——拉韦纳。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表明西罗马也早已将东罗马视为最大的对手了。
当匈人、东哥特人出现在一马平川的波河平原时,唯一能够保卫西罗马的,就是亚平宁山脉了。退守罗马,以亚平宁山脉为防线与阿提拉进行持久战,也是西罗马接下来的战略计划。然后让世人恐惧的“上帝之鞭”,在横扫波河平原后,却主动退回了匈牙利草原。而阿提拉本人,也在第二年(公元453年)神秘死亡了。关于阿提拉撤兵和死亡的原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就死因来说,比较流行和八卦的一个说法,是死在一位日耳曼公主的肚皮上。当然,这点就实在无法用地缘去分析了。大家知道这是一次“黑天鹅事件”就行了。
不过从地缘角度分析,撤军这一点倒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游牧民族军民不分,如果不是遇到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一般是在秋高马肥之时发动攻击的。不论在哪个季节攻击、得手与否,都需要很快撤回草原,否则将对游牧经济本身造成很大影响。作为西罗马的根基之地,征服意大利半岛全境的难度是显尔易见的。匈人骑兵可以横扫波河平原,但绝对不可能在一个攻击季越过亚平宁山脉,攻占罗马城。更何况从战略层面上看,意大利与草原的距离太过遥远了。草原内部的部落结构本来就松散,阿提拉如果深陷意大利的话,后方分裂的风险是很大的。
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在阿提拉死后,强大的阿提拉帝国便瞬间崩溃了。说起来,大家以后看历史资料时,也可以掌握一个规律,但凡以人名命名的帝国,寿数都很短暂(如亚历山大帝国、拿破仑帝国)。这种情况往往是某个英雄人物,抓住了一个战略机会,将版图迅速扩张到了违反地缘规律的程度。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败都在转瞬间。以草原的地缘影响力,本身是无法控制日耳曼尼亚、威胁意大利半岛的。从这个角度看,阿提拉已经做了件前无古人,且后无来者的事了。
当然,阿提拉帝国的崩溃,并不代表罗马或者日耳曼人,就此有机会反过来成为匈牙利或者南俄草原的主人了。只不过,日耳曼人终于有机会,在没有游牧势力的威胁下,考虑如何瓜分垂死帝国(西罗马)的问题了。那么,到底是谁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又是谁在日耳曼诸部中脱颖而出,抓住机会建立日耳曼帝国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一百零五节
西罗马帝国的崩溃
在日薄西山的西罗马帝国,总是会周期性上演王权争夺战的。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再一次被日耳曼军人所废。取而代之的日耳曼将领对于再维持一个名义上的西罗马帝国已无兴趣,转而希望通过宣誓效忠东罗马帝国,获得意大利国王的称号。按照正常的流程,已经习惯了东西分立的结构罗马人,会再派一个新皇帝接过西罗马的大统。
希望接棒西罗马帝位的,并不只有君士坦丁堡。最起码西罗马在高卢行省的驻军,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帮助西罗马帝国恢复秩序。然而不管是东罗马还是西罗马残存的势力,很快都会发现,在西地中海重建西罗马帝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那些不需要考虑匈人压力的日耳曼王国,是不会放过这个历史机会了。
最先发难的是占据比利时高卢的法兰克人。公元486年,法兰克人击溃了仍然效忠于西罗马的高卢驻军,抢占了巴黎盆地这块高卢的“中原之地”。占得先机的法兰克王国遗留下了很多地缘遗产,其中将之前并不十分重要的巴黎,定为法兰克王国的都城,就是其中一笔。不过法兰克人并不是压跨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是东哥特人加上的。
如果不是因为潘诺尼亚的位置直接受制于匈人,东哥特人完全有机会像西哥特人一样,早点成为地缘政治舞台的主角的。现在来自匈牙利草原的压力已经骤然消失了,东哥特人自然也会希望向西扩张。基于地理位置,以及当日作为阿提拉的盟友入侵意大利的经历,意大利半岛成为了东哥特人的扩张方向。
公元488年,东哥特人由潘诺尼亚向意大利进军,并于5年之后彻底击败那些系出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竞争者,建立了包含意大利、潘诺尼亚、伊利里亚、西西里在内的“东哥特王国”。从地缘政治后果来看,东哥特人相当于阻止了东罗马帝国在西地中海的“复辟”;法兰克人则把西罗马最后的火种,熄灭在了高卢。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正式终结了西罗马帝国的国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出现西罗马皇帝了。
正因为如此,公元476年被认定为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之日。在此之后,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世纪。在这个新时代中,东地中海与亚洲的地缘关系,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日耳曼王国分割下的西地中海部分。之前还有“西罗马”这块神主牌位的“日耳曼罗马”时代,我们曾经形象的将之对比为中央之国的“春秋”时代。现在的话,无疑就是群雄争霸的“日耳曼战国”时代了。
当历史跨入公元6世纪时,西罗马帝国废墟上还矗立的主要日耳曼王国有如下几个:法兰克王国、西哥特王国、东哥特王国、勃艮第王国。其中最为强势的法兰克王国,不仅吞并了位于莱茵河中游,由阿拉曼尼人建立的“阿拉曼尼亚王国”,还成功的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取了法国西南部的加龙河流域(公元507年)。20多年之后,罗纳河流域的勃艮第王国,也成为了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不过这并不代表西哥特人完全退出了“法国”。塞文山脉之南,连接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沿海通道,仍然在西哥特人的控制之下。
法兰克人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他的边缘位置,使之背后没有强劲的对手。与法兰克王国一样,西哥特王国同样也是边缘位置的受益者。偏安一隅的位置,使得西哥特王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国运,直到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才告终结。相比之下,东哥特王国甚至北非的汪达尔王国,所面临的压力就要大的多了。因为它们直接面对的,是依旧统一的东地中海——拜占庭帝国。用“拜占庭”指向中世纪的东罗马帝国,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为的是将之与东、西罗马分立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区分开。事实上通过后面的解读,大家也会明白,中世纪的“拜占庭”虽然仍在消费着罗马帝国的政治遗产,但从本质上看,无已是旧瓶装新酒了。
尽管我们通过回顾历史,已经看到拜占庭帝国的走向了,但最起码在中世纪伊始,东地中海的罗马人,还是认为自己有机会从日耳曼人手上,夺回西地中海的控制权的。相比日耳曼人的战国格局,拜占庭帝国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一则帝国完整保有了罗马帝国在东部的疆土;二则新生的帝国却亚洲君主制文化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集权了。另外,阿拉提帝国的崩溃,不仅让日耳曼人的受益,也让君士坦丁堡方面的北方压力得以消失。这些因素使得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能够在资源和效率上,压倒任何一个日耳曼王国。
公元6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相继攻灭与之地理距离最近的汪达尔王国和东哥特王国,甚至在伊比利亚半岛东南部登陆,把战火烧进了西哥特王国。这一时期也是拜占庭帝国的疆土最盛之时,离重新将地中海变为内湖仅一步之遥。基于这一成就,发动这一系列战争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年-565年在位),在后世也被冠以了“大帝”之号。然而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并不是一个边缘地区。在其尽力从日耳曼人手中,“收复”西罗马故地时,东面的萨珊波斯也同样希望,能够从罗马人手中“收复”波斯帝国在亚、非两洲的历史疆域。
尴尬的地缘位置,使得拜占庭帝国不得不在战略上,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在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间,除了对西方的日耳曼诸王国展开攻击外,他与萨珊波斯之间就前后进行了两场战争。很显然,拜占庭帝国并无法在这两线战争中,都取得全胜。事实上,新生的罗马能够在中世纪开启之季表现突出,很大程度是因为日耳曼世界还处于混乱之中。一旦日耳曼人内部在一定层面上完成整合,拜占庭帝国很可能就是一个悲剧了。那么日耳曼诸王国之中,有没有机会也出现一位“大帝”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一百零六节
伦巴第人与拜占庭帝国
就中世纪开始时的情况来看,东、西哥特与法兰克王国,显然是日耳曼人中最有力的竞争者。东罗马的小宇宙爆发,让东哥特王国退出了竞争者行列。不过这并不代表欧洲大陆的“日耳曼三国”时代的结束,因为与意大利半岛一山之隔的日耳曼尼亚,永远不缺乏想到地中海晒太阳的部族。拜占庭帝国的这个高峰期(查士丁尼时代)一过,大批日耳曼人旋即开始了新一拔的入侵。
这次日耳曼入侵的领导者,是一支叫做“伦巴第”(又译“伦巴底”)的日耳曼部落。伦巴第人南迁的路径,与其他日耳曼部落并无二至。他们最早沿易北河南下进入日耳曼尼亚南部,定居于奥地利一带。在东哥特人入主意大利之后,随之填补了其在潘诺尼亚留下的空白。现在东哥特王国已经被拜占庭攻灭,而罗马人又后劲不足,伦巴第人的机会也就到来了。然而伦巴第人并没有取得如哥特人那样的成就,因为直到2个世纪后,伦巴第王国从政治版图上消失,他们也未能统一整个意大利半岛。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拜占庭帝国并未完全退出意大利。
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已经被一些研究者认为进入“希腊化时代”了。不过所谓的“希腊化”,并非指罗马的政治、文化形态被“希腊化”了。事实上,经过罗马数百年的经营,已经没有人会以希腊人,或者希腊文化的传承者自居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只会以自己是罗马人为荣。参考中央之国的情况,大家应该能更好的理解这点。当中央之国的概念覆盖到长江流域之后,即使某个中原王朝被迫南迁,也不会就此认为自己系出吴越或者楚文化。相反,无论是政权还是民众,都会更加强调自己的“中原”身份,以求最大限度的继承巅峰期的地缘遗产。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所谓的“希腊化”是新帝国已经正视了自己的地缘定位,即拜占庭帝国只能以希腊半岛为根基之地,统治半个地中海的现实。只不过西罗马既然已经不存在了,这“半个地中海”的概念,也就不必作茧自缚的去遵守东、西罗马的政治分割线了,除非日耳曼人有能力把拜占庭帝国赶回东地中海。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最为有利的情况是,他们已经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了以突尼斯为核心的迦太基故地。利用这个基地与希腊半岛形成的犄角之势,拜占庭帝国最起码在“大希腊地区”(意大利半岛南部及西西里岛)能够拥有明显的地缘优势。
除了大希腊地区,伊利里亚沿岸,以及意大利半岛东北部的威尼斯、西部的那不勒斯一带,拜占庭还顽强的保有一些拥有海岸线的飞地。虽然从技术上看,支撑这一切存在的,显然是拜占庭帝国的海上优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君士坦丁堡方面的海军实力,有什么重大突破。恰恰相反,相比罗马的黄金年代,拜占庭的海军是大大退步了。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优势,首先是因为它有维持一支海军存在的“刚需”。由于领土地跨欧亚非三洲的格局,即使仅仅出于内部结构稳定的需求,拜占庭也需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海上运输力量(包括保护它们的舰队)。
反观拜占庭在西地中海的对手,却并没有建立一个地中海帝国的野心和需求。唯一能够在海上给拜占庭帝国造成麻烦的,只有一些日耳曼海盗。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欧洲的地缘政治板块出现了质的变化。高卢、日耳曼尼亚地区不再是可以舍弃的边缘板块,而是日耳曼政治版图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地缘博弈重心,不可避免的从地中海沿岸地区,转向欧洲大陆腹地。地中海的地缘价值也转变为一个只需注意岸基防御的边缘海,而不是一个承担互联互通任务的“中心湖”了。
从西罗马帝国寿终正寝算起,日耳曼世界的这个战国时代,前后大约经历了220多年时间。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里加冕为皇帝。日耳曼人也终于迎来的他们的第一位大帝——查里曼(查里大帝)。
|